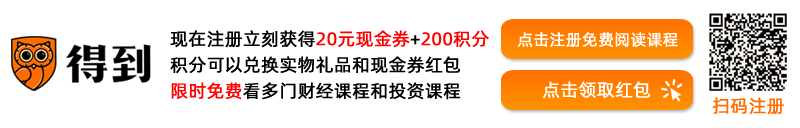為什麼說政策拐點是經濟拐點的前奏?

今天我們談一個關於觀察中國經濟信號的重要工具,就是怎麼去判斷經濟拐點要出現?這個問題很複雜,觀察維度也很多,但既然我們是講政策趨勢的專欄,我們就政策這個維度,談如何看到經濟拐點的信號。簡單說,在經濟拐點之前,要先看到政策拐點,在經濟觸底反彈之前,要先找到“政策底”。接下來我詳細解釋下。
政策預期管理的“美聯儲化”轉型
最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到,高層的相關會議、部委的新聞發布會,以及各種政策的出台,變得越來越頻繁。
比如,從2024年9月24日到10月20日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就有一場中央政治局會議、三場國務院常務會議、一場總理座談會,以及超過7場國新辦的部委新聞發布會。幾乎是以三四天一場的頻率在積極和外界溝通政策。
除了中央高層外,央行、金融監管總局、證監會、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住建部、司法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工信部也輪番登場。
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呢?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極其關鍵的轉變,就是我們國家政策的預期管理正在越來越“美聯儲化”。
美聯儲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擅長搞預期管理的。當市場處於分歧期時,美聯儲會希望“凝聚共識”,通過多渠道的信號釋放,讓市場及早領會美聯儲政策意圖,從而提前調整自身行為,減少市場波動和政策衝擊。而當市場處於情緒一致期時,比如所有人都很狂熱的時候,美聯儲則會潑冷水“打散共識”,避免市場對貨幣政策過多押注和投機。
兩個具體印證
中國政策的預期管理“美聯儲化”可不是一件小事。這背後反映的,是中國政策系統的靈敏度大幅提高。簡單說,我們的政策正在越來越快地回應公眾關切和公眾情緒。
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例子是2024年八九月份的時候,關於創投退出難這個問題引發了極大討論。
一邊是股市ipo收緊,pe(私募股權)/vc(風險投資)創投基金們無法通過上市來實現退出,股份無法變現。
而另一邊則是基金到期,大量投資者要求贖回本金。無奈之下,創投公司們只能“反目成仇”,把自己投資的企業告上法庭,要求企業按照合同上的回購條款,立即回購股份,返還投資款。根據禮豐事務所的統計,大約有超過13萬個創業項目、約8萬億的資金面臨退出壓力和訴訟風險。如果真演變成一場踩踏式、擠兌式的起訴退出潮,我們失去的可能將是一整代的創業企業家。
可喜的是,政策立即作出了反應–9月的國務院常務會上,總理李強做出了一系列部署來緩解創投踩踏危機,包括放鬆科技企業ipo、大力推動市場併購、推廣實物分配股票、設立區域性股權轉讓市場、大力推動s基金等等,就是要對市場當下的實際矛盾和聚集的情緒進行處理。回應可以說十分迅速。
第二個例子是政策對於民營企業關切和情緒的反應。
本來面對貿易戰,疫情衝擊,債務爆雷頻發,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們已經壓力山大了。但壓力不僅僅來自企業收入和利潤下滑,2024年以來,有幾個比較典型的現象:
第一是一些財政困難的地方政府賴帳,拖欠民營企業帳款;
第二是部分地方政府在財政緊縮的情況下,有強烈的對企業嚴苛執法、靠罰款來彌補財政缺口的傾向;
第三是一些地方政府搞趨利性執法,把手伸向經濟發達地區,不規範地異地執法,以涉案為由凍結民營企業帳戶,帶走企業家。這種亂象俗稱為“遠洋捕撈”。
這些亂象打擊了市場的情緒,以及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中央很快捕捉到了這些信息,並給出反應–比如從建立全國拖欠帳款統一清繳平台到嚴令各地約束“以罰增收”行為,再到總理和國家發改委主任直接公開釋放信號,要求嚴格規範異地執法,隨後就是《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草案出台,從法律上確保大家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在安全和發展上的穩定預期。
總之,以上兩個例子反映出,政策信號的反應周期,越來越快。
從這幾件事我們可以做個總結:
政策制定者在越來越靈敏地關注著當前的市場和輿論動向,甚至是社會情緒,並希望通過及時、迅速的回應來消除負面影響,建立預期導向,努力實現政策與公眾期待的同頻共振。
換句話說,可以做個結論:自下而上的信息傳導路徑在縮短,而自上而下的政策回應靈敏度在放大。
政策拐點與經濟復甦的關鍵關係
剛才我們說了這麼多的政策案例,跟大家有什麼具體的關係呢?我們進一步推導,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信號,就是政策系統靈敏度提升的背後其實就是政策的拐點,用股民的話說,叫“政策底”。
鑑於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本身政策的巨大作用,政策的拐點在相當程度上意味著經濟的拐點。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雖然政策的拐點不一定很快帶來經濟的拐點,但沒有政策的拐點,則基本無法預見經濟的拐點。或者換句話說,至少要先有政策的拐點,你才能期待經濟的拐點。
而政策拐點的出現,對現實越來越迅速的關切和回應,往往意味著新一輪的寬鬆局面。我再強調一遍,對社會關切的及時回應導致政策靈敏度增加,而靈敏度增加的結果往往就是新一輪的寬鬆。
比如2008年後,政策為了挽救經濟受到的外部衝擊,選擇放鬆土地財政,允許各地通過賣地和成立城投來籌措資金。
如果放在現在的視角,肯定會覺得,當時這麼做導致了後來的很多問題。但如果我們代入當時的視角的話,其實可以發現,當時各方面投資意願極低,錢全部瘀堵在銀行中不願出來。而正是由於政策轉向寬鬆,才把地方政府和市場上各類企業的積極性、主動性給調動了起來,大家才有動力去搞擴張和投資,而擴張投資又慢慢帶動沉澱資金走出銀行,最終讓中國率先走出了全球次貸危機。
回到當下,我們再一次迎來政策的拐點,或者說政策底,而且這一次的寬鬆會是一種更加全面和高維度的寬鬆,包括貨幣寬鬆、涉企輿論寬鬆、司法寬鬆等等。
另外,我們觀察以上的這幾個歷史時期可以發現,每一次政策拐點出現後,下一步便是尋找抓手。2008年的抓手是地方政府,通過地方政府的投資帶動經濟走出困境。2014年的抓手是居民,通過居民的購買力來消化房地產庫存。
而放在當下,我認為,這次政策的拐點出現後,下一步最有可能的抓手就是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前者被給予了很多重大戰略任務,後者最近也正在被政策大力度“促進”和“激活”,希望從市場端起到更關鍵的作用。
從三中全會決定文件到最近的《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給民營經濟提供關鍵的信心,安定的環境,釋放和激發其活力,進而通過市場活力一體解決科技、就業、稅收等多重問題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這一切將帶來一些重大的影響:因為政策靈敏度的提高,市場的關注和情緒能夠更快地上達,高層的決策和政策也能夠更快地傳遞給市場,帶來更大的寬鬆和活力,而寬鬆和活力最終會大幅度優化大家的“體感”。不要小瞧這個“體感”,“體感”的改善,會更直接地影響市場的預期和信心的修復。
而只有信心,才能讓中國經濟復甦真正到來。
原文網址:https://zh.gushiio.com/fenxi/426.html